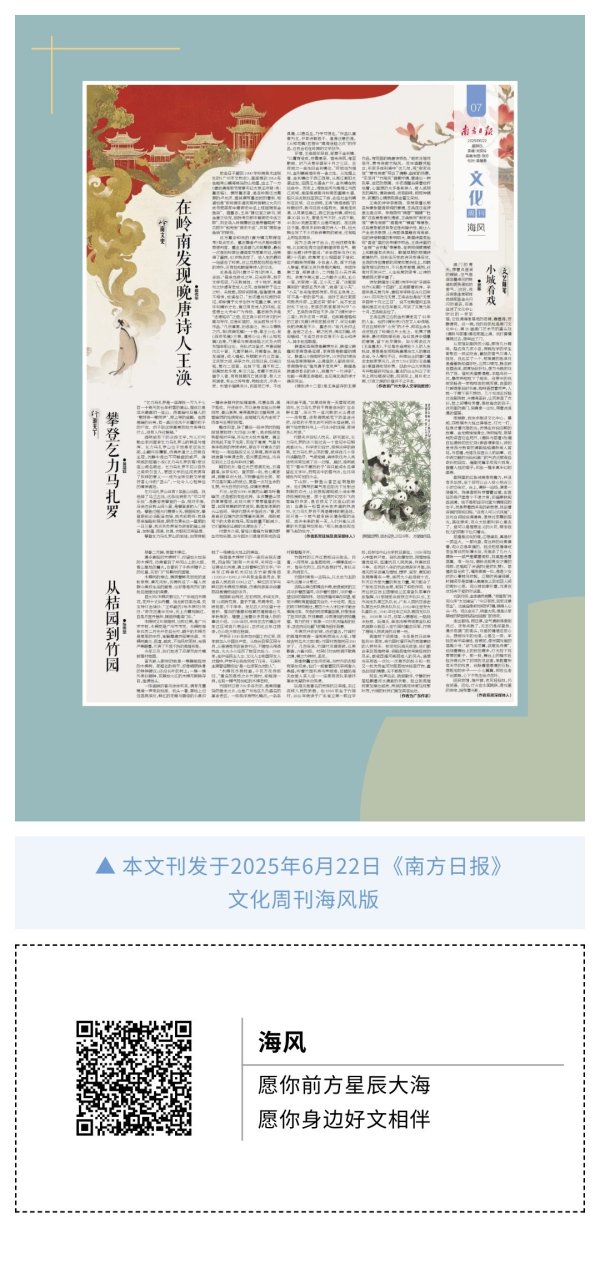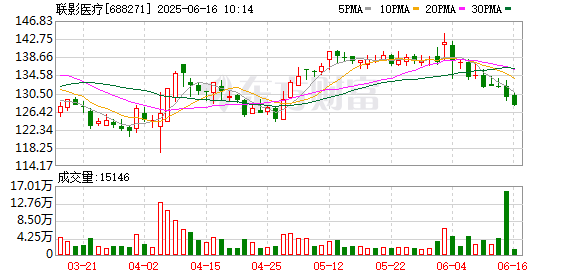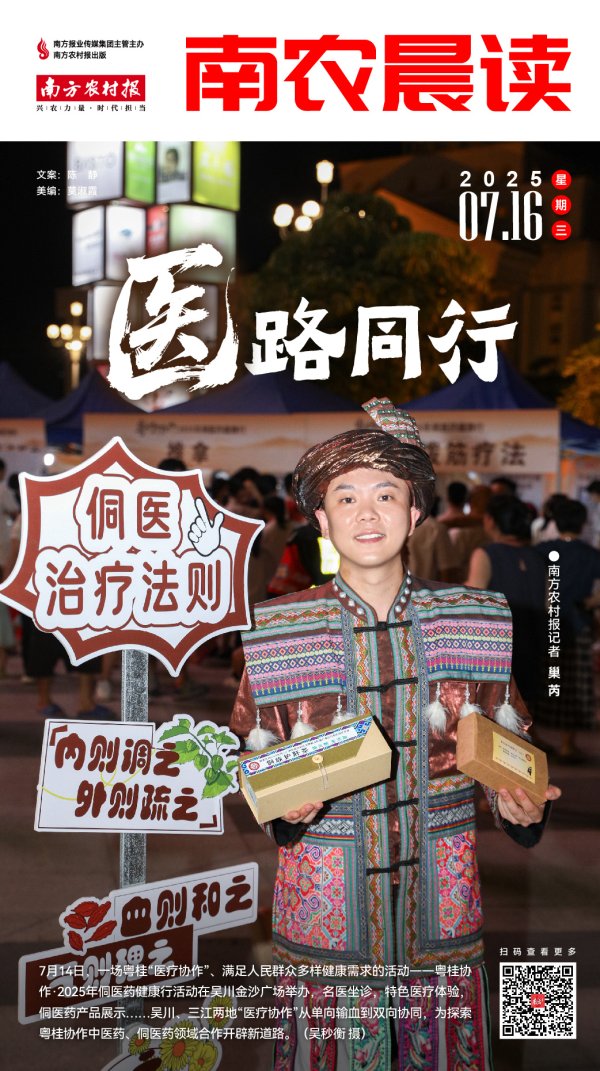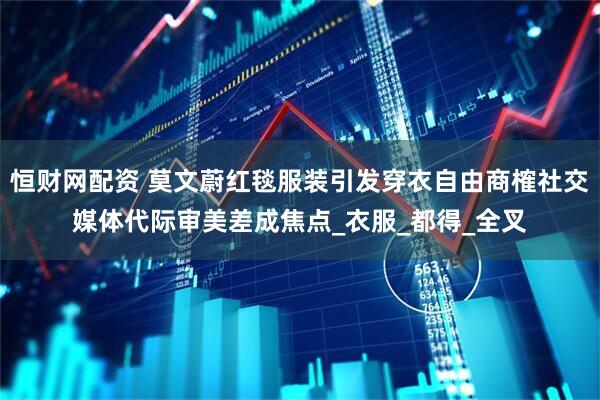“成群的参天大树底下,基层医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佛山市禅城区,破旧的办公桌旁,一座镇街级医院的话事人平静说出凛冽的话语。
这番表达,折射出佛山镇街医疗体系的深层矛盾。作为全国医改“真抓实干”先进城市,佛山构建了“市优、区强、镇活、村稳”的四级医疗网络,全市32个镇街中27个设有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覆盖率84%。但数据背后,医疗资源“倒三角”配置、医保控费高压与人才结构性流失,是镇街、社区级医疗机构面临挑战的另一样貌。
基层医院运营
“增诊不增收”的挑战与应对
作为全省医疗“第三城”,佛山市的医疗资源增长仍在“快车道”。佛山市卫健局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市医疗卫生机构3309家,比2023年增加226家,增长7.3%;床位数45058张,同比增加2810张,增长6.7%。与之对应,全市诊疗人次同比增长9.04%,基层诊疗人次同比增长9.88%。从全市来看,镇级及以下诊疗量占比为57.96%,基层诊疗人次增长高于平均水平。
然而,“增诊不增收”,是目前部分基层医院的运营现状。
以佛山市中心的某镇街医院为例,2024年,其住院人次同比增长22.91%,门诊人次增长16.51%,但医疗业务收入同比减少6.44%。
多位基层医院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原因在于医保政策的制约和财政投入的相对不足。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改革之后,医保按总额或病种付费,医院费用控制严格,超出额度须自行承担,且报销名目年年更改,合规压力大。这导致医院在努力增加患者的同时,还要考虑成本控制,否则可能陷入亏损。
“DRG结余激励下,2023年我院主动缩减20%的高成本手术,但患者外流率增加15%,在控费和留住患者间找平衡点仍是难题”,佛山一社区医院院长日前公开表达了这一困境。
另一方面,基层医院收入主要来源于医保收入和公共卫生财政拨款(部分社区卫生中心为全额拨款)。2019年鳄鱼配资,佛山市实施高水平医院“登峰计划”,投入16亿元重点培育和建设11家高水平医院,相对市级大医院,财政对于基层医院的投入倾斜不足,难以兼顾,基层医疗机构设备设施更新困难,容易陷入医疗水平发展迟缓、医疗供给不足、失去社会认可的恶性循环。
“受制于经费的紧张,数年间,我们还没有进行过医疗仪器的更新,因为发展基金十分有限,只能用在最紧迫的地方”,禅城区一位基层医院负责人如是说。
内卷竞争
竞争格局下的基层医疗机构定位
地图搜索框输入“医院”,密集的坐标说明,部分镇街医院,尤其是位于市中心的镇街医院不得不直面激烈竞争。目前,佛山市有13家三甲医院,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绿岛湖新院区、珠江医院三水医院新城院区、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大良院区)、佛山市顺德区妇幼保健院马冈院区、佛山市中医院等医院还在不断“攻城略地”,市中心高密度聚集了优质医疗资源。
由于特殊地理位置,佛山还不得不面临隔壁广州强势医疗资源的“虹吸”。广州有60余家三甲医院,且大多分布在越秀、荔湾、番禺白云等距佛山较近的片区。不过,两地医保“不互通”建立了“隔离墙”。佛山卫健局披露,2023年佛山市域内就诊率保持在99%以上,近3年市域内住院率均在95%左右。
佛山基层医疗机构间不得不直接与三甲医院、民营医疗机构等“争患者”,部分服务同质化形成“内卷”。一位基层医院负责人表示:对于佛山市整体医疗资源是否过剩不好评价,但就中心城区的基层医疗机构体感而言,“生存是紧张的,资源是过剩的”,公办医院和民营医疗机构年年增加,竞争十分激烈。

南都记者发现,佛山市人民政府约5公里范围内,聚集了佛山市中医院,佛山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人民医院,复星禅城医院,佛山市妇幼保健院等大型三甲医院,中间夹杂镇街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广东省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3》显示(来源:医院咨询新知公众号),2014-2023年间,佛山市全市医院类机构增长42家,但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仅增长24万人,近9年病床使用率降低13%。这从侧面反映出,地区医疗机构间的竞争正在加剧。
“影响医院吸引力的‘最大变量’是患者的就医习惯,人们都喜欢‘往大医院跑’或者‘找熟人’,病情较轻的患者多在经济因素考量下才回到基层康复,这是现状”,一位有几十年基层医院工作经验的业内人士说。
值得注意的是,佛山基层医院的生存状况伴随地区差别也有显著不同。一些医疗资源聚集度相对一般的地区,基层医院体系仍占据着重要地位。一位非中心城区的基层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院近两年基层诊疗量增加,营收基本稳定且能覆盖支出,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完成设施完善和硬件提升。此外,部分社区卫生中心为全额拨款,以完成地区医疗服务指标为核心目标,得益于紧密医患关系的建立和站点广布的便利性,其运营压力相对较小。
基层人才引育
机制创新与职业吸引力提升鳄鱼配资
南都记者走访发现,部分镇街级医院的人才梯队呈现“青黄不接”的状态。
“过去能招到三甲医院的老主任,如今招本科生都有难度,人才梯队面临断层,新生代医务人员水平不及过往”,一位基层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
薪酬鸿沟引发持续失血。千镇千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研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基层护士月均收入4800-6500元,绩效工资占比不足30%,与同城大型公立医院待遇有明显差距。这种情况也有特例,顺德区乐从医院2024年底的招聘启事披露,该院医生年平均薪酬23万~25万元,护士年平均薪酬15万~18万元,编内编外人员工资绩效待遇实现“同工同酬”。
南都记者还了解到,佛山部分镇街医院招聘时由于无法提供编制,对于医生的吸引力大大减弱。记者搜索近期招聘信息发现,禅城区人民医院南庄医院招聘急诊科医师、康复医学科医师、护士等6人,均为合同制工作人员。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附属杏坛医院、狮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近期也公开招聘非编工作人员。
“招聘高端人才有困难,主要原因是薪酬相对固定且低于地区医院,平台低、在行业内部认可度有待提高。”佛山某社区卫生中心负责人说。
此前,农工党佛山市委会在预提交的提案中也关注到了医疗卫生人才短缺的问题。提案指出,目前佛山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员总体不足、留不住人才的问题仍然存在。
基层差异化发展
特色服务与整合创优的实践
“镇街基层医院想要破局,一定要立足本区域,做好差异化服务”,多家佛山镇街医院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佛山市卫健局披露:“强基”行动下,过去一年佛山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创优项目,全市共有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达到创建国家推荐标准,占比近六成,位列全省第三,在区镇医院培育148个临床重点(特色)专科,2024年新增推广26项卫生健康适宜技术下基层,累计135项。
以张槎医院为例,其通过中医特色专科(如治未病科、老年医学科)等,张槎居民满意度明显提升。近两年,该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大力推广中医适宜技术。自2023年4月在下属卫生站推广后,短短4个月中医适宜技术业务量激增9倍,全年社区卫生站中医适宜技术业务量较2022年增长超800%,2024年传统中医治疗和康复理疗项目收入分别增长67.20%、0.81%。
南海区丹灶镇有25万常住人口,但仅有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和丹灶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家公立医疗机构。南海八院有中医科、骨科(脊柱微创治疗专科)等特色专科和名医、名科,三甲医院专家定期到镇内坐诊;社卫中心则拥有15个站和2个延伸点,提供更加精准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该镇基层医疗资源在2023年进行了一次系统整合,南海八院和社卫组成“医联体”,开启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发挥一个善于“上扬”,一个善于“下沉”的优势。
发力慢性病预防,“治未病”是基层医疗预防体系的优势所在。制造业重镇顺德创新探索实施“五医”融合,即医防融合、医育融合、医校融合、医企融合、医养融合,为婴幼儿、青少年、中年、老年等全人群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家门口”医养结合服务模式,10个镇(街道)公办医养结合机构全覆盖,充分发挥基层医疗体系的“强链接”。数据显示,2024年顺德基层诊疗量较2022年增长37.4%,节省群众医药费用608万元。
大沥的三家镇街级公立医院则尝试“合并创三甲”,用抱团的竞争优势参与更广阔的市场竞争。其还引入高校科研资源,挂牌“佛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服务将覆盖南海东部超百万群众。当然,医院合并是一把双刃剑,管得好,可以提升医院综合实力;管不好,则可能弱化医疗服务能力。
基层医院点位分布的“近距离”以及“家庭医生”服务制度的长期作用,使其与本土群众有更紧密的联系,受制于资金规模、投入强度,无法与拥有规模化、高技术优势的大医院直接“抗衡”。纵观张槎、丹灶及顺德基层医院能够稳住基本盘的要义在于,其专注开展差异化特色诊疗服务,结合本地人口结构、疾病图谱精准定位需求,最终以“在地化能力”形成基层医疗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其借助“疾病预防”政策配套的支持,通过强有力的整合创优,方能在市场站稳脚跟。
“强基”固本
政策支持与体系优化的方向
近年来,针对基层医院的发展困境,佛山也在大力实施国家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达标-创优-提质”。如,网格化布局全市医疗联合体建设,全市共35家二级及以上医院与全部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建立对口协作关系;同时,市一医院全面托管高明区人民医院、三水区乐平镇人民医院。
良好的“医联体”合作确实可以带动基层医院发展,不少基层医院负责人透露,加入“医联体”后,“双向转诊”制度更为畅通,基层医院能够得到资源赋能,大医院实现压力纾解。如,张槎医院曾托管于佛山市中医院,中医院派出部分学科专家定期到张槎医院坐诊,有效带动医院的技术服务水平提高和收益增长。不过,2024年9月,张槎医院与佛山中医院解除托管,更名为禅城区人民医院张槎医院。
医联体的本质是通过合作共享、共建、共赢等,让区域内的医疗服务更加有效和通畅,医共体则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县域医疗服务体系。显然,其十分考验制度设计。若利益不合,或财务管控过严、技术垄断,一些“散伙”,一些“水土不服”,一些“侵蚀原有根基”,有可能变“造血式帮扶”为“掠夺式侵占”。所以,如何使技术下沉需伴随能力转移,资源整合同时要尊重基层功能,或许是佛山医改的重要努力方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一些地方如莆田市也在今年年初实行《莆田市分级诊疗促进条例》,引导常见病、多发病和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首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保政策的导向是关乎基层医疗体系如何发展的重要“风向标”。据了解,当前佛山医保政策对基层相对有倾斜,基层医疗机构医保报销比例可达90%。
然而,推动分级诊疗并不容易。随着大医院扩张、交通和信息的便捷、异地就医医保支付渠道畅通等种种社会变化,患者越来越习惯寻求优质医疗资源服务,演变成“小病去三甲”的态势。正如某位业内人士所言:“让医保制度真正推动‘基层首诊’,激励医院放手做好群众服务,将发挥基层医疗体系的更大价值。”
面临“内卷”生态,呼唤“破局之道”,这是佛山市多家基层医疗机构的普遍体感,也是全国医疗体系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一个侧影。在这场佛山医疗系统的“暗战”中,基层医院机构如同被裹挟的瓦砾,但他们仍在努力扎根求生,撒下一片荫凉。
采写:南都记者 孙振凌 李焕怡鳄鱼配资
兴盛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